阅读:0
听报道
这些年来,怀念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年代似乎是一个流行的风潮,一直有许多人对八十年代情有独钟。人们往往觉得今天是一个并不浪漫和富于诗意的时代,但是,今天中国的崛起所具有的力量和我们的社会文化状况其实是八十年代根本无法想像的。四十年的光阴仿佛一晃而过,我们还没有抓住八十年代,现在已经是“90后”和“00后”而在今天的“新世纪”和我们所缅怀的八十年代之间,其实有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历史的关键的转折的年代,也是我们回顾这四十年的历史的时候需要时时关切的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意义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越来越被我们所感受到了。虽然人们好像还是很不情愿提到这个时期,似乎它的意义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不少人觉得那个时期,好像有些不仅合乎他们的理想,仿佛这是八十年代在向下坠落,是激情和热情消退,平庸到来的时期。其实对于历史来说,这个时代的意义似乎是被今天的人们低估了。这种低估其实是来自我们对于我们今天所缺少的东西的渴望。这渴望导致了我们不愿意提及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其实是一个关键的转变的时期,是中国的未来由朦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关键的时代,正是由于有了九十年代的文化的转变,我们其实才可以进入一个新世纪,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才会有今天的成果今天看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是三十年来中国发展的一个过渡的时期,有了这个时期,八十年代的价值才会转化为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国的发展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未来。所以,九十年代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新周刊》就是出现在那个时代,现在愿意出一本书,从当下对那个时代提出新的思考和新的见证,这无疑具有着独到的意义和价值。
遥想当年,中国八十年代末的巨变刚刚过去,“南巡”所激荡的风潮和新的期望才刚刚被诱发,下海经商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机关里的人们才刚刚开始创业。今天的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如马云、马化腾等等都还是我们所预想不到的未来。而王健林等人也才刚刚开始自己的事业。而从《渴望》到《北京人在纽约》直到《还珠格格》,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的记忆所在。当年《渴望》主题曲那流传在大江南北的歌声到今天让我们仍然感到当年的那种社会的集体意识:“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这是一个真正开启了日常生活的感觉的新的时代。那些宏大的叙事开始远了,新的生活的欲望和情绪开始出现。这是新的以大众为中心的社会。它们显然提供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景观,也超出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性”的话语。它的形态是我们必须认知的关键。无论是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还是王朔的作品,或是《渴望》《北京人在纽约》这样的电视剧,或者如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长恨歌》、莫言的《丰乳肥臀》等等的小说都提供了变化的轨迹。
知识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一些对于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的知识分子焦虑于在新的市场化的环境下是否会出现一个社会崩溃的“旷野上的废墟”,并为此发出异常激烈的“抵抗投降”的狂热的呼叫的时刻;是一些人对于急剧市场化和全球化 的未来把握不定,也对于中国的前景犹疑困惑的时刻;这也是另外一些人对于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更多的信心和更加明智的分析的时刻。于是知识分子的大论战正是凸现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同的思考和观察。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刚刚进入所谓的“后新时期”,消费社会才有了一个雏形,社会还处在刚刚处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前期。中国的发展的许多今天看起来简单的事实,在当年还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今天看来所谓“后现代”,所谓“全球化”或“中产群体”都早就是老生常谈了。在当年却仍然是受到了众多的置疑和追问的难以接受的事情。这里的进程的背景是异常清晰的:一方面,中国变化完全超越了原有在“新时期”的构想和预设,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的进程中的位置也有了以往根本无法想象的独特性。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竟然是从美国特朗普所鼓动起的“逆全球化”的浪潮在发挥作用。
认识九十年代,我们首先需要从八十年代开始。八十年代的中国刚刚从“文革”中脱离出来,正处在一个精神解放的时代。当时的人们把一切都视为精神解放的表征,一件牛仔裤,一副“蛤蟆镜”都意味着从精神上摆脱压抑,需求新的空间的努力。其实八十年代的主题,就是如何将个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宏大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出来。八十年代的“主体性”的召唤表达出来就是这种“个人”存在的精神性的要求。无论是萨特还是弗洛伊德其实都是为这个新的“个人”的出现发出的召唤。这个“主体性”的个人的展开,直接提供了思想和精神从原有的秩序中“解放”的想象。其实,八十年代文化的关键正是在于一种对于康德的“主体性”观念的新的展开。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的1984年版有一个异常重要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八十年代思想的核心的 命题。李在这篇文章中点明:康德的体系“把人性(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批判哲学的批判》1984年 424页)。而李泽厚的发挥似乎更加重要:“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同上,434页)这里李泽厚召唤的康德的幽灵其实是对于八十年代新的精神的召唤。“主体性”正是整个八十年代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话语中脱离的基础。而这个“主体性”正是新的“现代性”的展开的前提。八十年代其实具体地展现了这一“主体性”的话语。正是这种 “主体性”的寻找,变成了八十年代的“现代性”赋予我们的最大的梦想。
进入九十年代,世界和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时期”追求的目标仿佛就要实现,但它本身又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历史根本没有按照预想的道路前行。在“冷战后”的新的世界格局和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国的状况成为世界的焦点。中国的九十年代的文化经验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后新时期”中,中国经历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是极其深刻的,它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导致了高速的经济成长,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新问题。中国以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式在九十年代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一方面是政治性的象征系统维持不变,以作为社会避免急剧变化过程中的混乱的策略,随着苏联、东欧雪崩式瓦解和十年来俄罗斯的持续危机以及国际竞争的激化,民众的国家认同也有所凝聚;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对于社会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已经极大削弱,国家直接控制的工业资源已经不到30%,传统的“单位”体制已经越来越弱化,跨国企业和民间资本已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舞台。而在越来越市场化的社会舆论和大众文化的主导下的所谓“公共空间”也已经迅速形成。人们的生活经验已经不可能处于国家的全面控制中,而是明显地处于一种横向的联系之中,市民社会已经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开始形成,而随着大量移民的出现及互联网的发展和国际投资的剧烈增长,中国的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目前,中国在全球化之中无疑早已不再是一个全能的社会,而是一个社会的“横”向的关系和国家的象征及”纵”向管理交错的复杂的社会。
九十年代的文化的特点就在于一种“物质性”的出现。没有物质性的变化,我们就不可能有新的未来。虽然我们可能丢失八十年代宝贵的东西,但这丢失却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必然。八十年代的文化中我们的想象是建立在精神的基础上的,我们好像是用头脑站立在世界上,我们虽然仍然面对匮乏的生活和新的来自外界的物质性的诱惑,但我们的纯粹的精神追求和抽象的理想支撑了我们的想象和追问。所以,八十年代的“新时期”虽然有极大的物质性的吸引的背景,却是在精神的层面上展开自身的,它依然是不及物的。这里的追求几乎忽略了“物质”的诱惑和吸引。但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却是将八十年代的抽象的精神转变为物质的追求。最初的消费的诱惑的力量,也凸显了当年抽象的“主体性”今天在现实的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的困局。这是将康德的玄虚的用头脑站立的状态,转变为用双腿支撑自己的“主体性”。
其实,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其实在断裂中自有其连续性。九十年代将八十年代抽象的“主体”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个人”,八十年代的“主体”是以抽象的精神进入世界的,它仅仅表达了一个真诚而单纯的愿望,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展开。它的没有物质支撑的空洞性,正需要九十年代的填充。而九十年代的这些中国的“个人”以实实在在的劳动力加入了世界,用自己的具体的劳动和低廉的收入寻找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世界。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正是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给了抽象的八十年代一个具体的、感性的现实。八十年代的那些抽象而浪漫的观念正是被九十年代的消费愿望和物质追求所具体化的。八十年代康德的自由的“主体”变成了九十年代黑格尔式的“理性的诡计”拨弄下的“个人”。这些个人的成长和变化其实正是今天社会凝聚和发扬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九十年代开启了二十一世纪的未来。
而中国内部的变化正是全球的变化,全球化其实正是需要中国的参与,而中国的发展本身也必然带来新的可能性。九十年代中国内部和外部所展开的”物质性”的力量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力量,也是中国最坚实的基础。九十年代超越八十年代的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它终结了八十年代抽象玄虚的“主体”,而是寻找到了一个“主体”赖以存在的前提。
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全球化的进程其实是历史的新的一页。它一方面告别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也超越了五四以来反抗西方的宏大叙事,而是在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中探寻新的方向。今天的中国的丰富而复杂的形态,正是那个时代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或者所感叹的一切中其实都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的影子。今天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和力量,正是九十年代的开放所奠定的。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在那个时代出生的青年已经成了今天的主人翁。一切都变了,我们从今天回望那个时代,那些回忆好像远了,也好像就在眼前。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正是从那里来的。我想,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活着,它仍然在我们之中发挥影响。
让我们从这本书回到九十年代,在回忆中领略那过去,而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也可以从这部书回到那个时代,那依然活在我们之中的时代。
是为序。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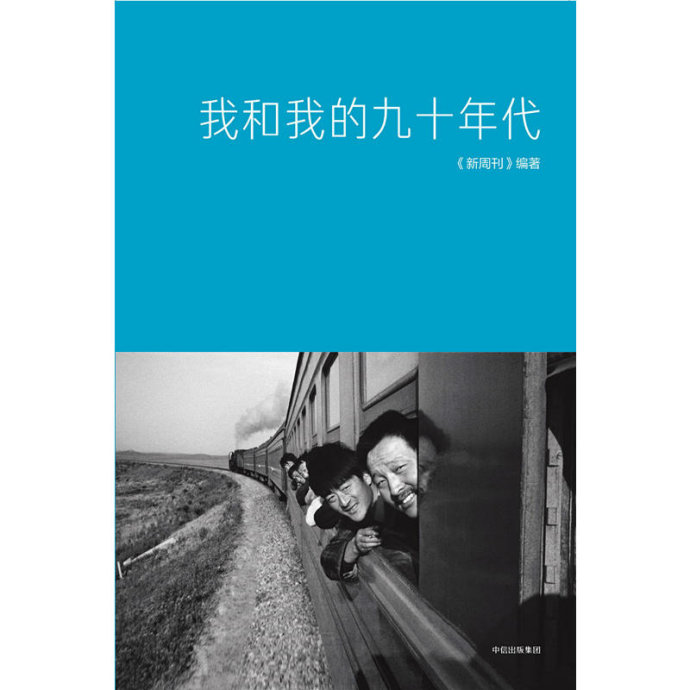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